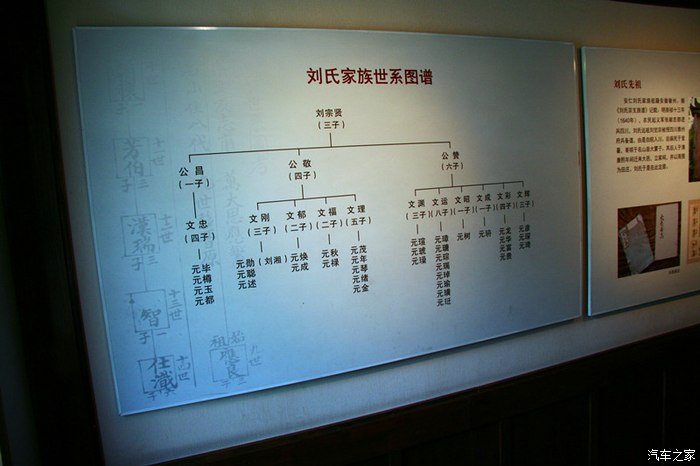:经典与经典注疏的建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我们在关注当下中国的同时,也应将中华文明的古代发展史纳入研究视域之中,在古今之变与中西之别的宏观视野中,构建独特的中国文化形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研究孔子、研究儒学,是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认识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历史来由的一个重要途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它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经典与经典注疏的建构
众所周知,传统儒家学者们所面对的“经典”文本是十分有限的。《庄子·天运篇》即已记载《诗》《书》《礼》《易》《乐》《春秋》,合称为“六经”,由于《乐》失传,自汉以来,儒家“五经”体系得以建构。唐初以后,再加上《周礼》《仪礼》以及将《春秋》分为《公羊传》《谷梁传》《左传》,“五经”逐渐演变成“九经”,南宋时期再纳《论语》《孟子》《尔雅》《孝经》入经,形成了儒家“十三经”的经典体系。
中国古典儒家哲学思想体系的流变基本呈现于历代经学家对这些数量有限的经典文本的诠释中。汉代大儒郑玄即以“遍注群经”为己任。此后随着王朝更迭,战乱频仍,典籍四散漂流。至唐代时,孔颖达等经学家受命编纂《五经正义》,仍聚焦于对这些有限经典文本的注疏。宋代,无论是北宋的二程(程颢、程颐),还是南宋的朱熹,皆以经典注疏为其为学的方向。及至明代心学,阳明所留著述,除去后学对其言行的记录及其与友人的通信,唯有一篇口述的《大学问》和《五经臆说》残卷留存,仍旧是对经典的诠释文本。清代《十三经注疏》的编成,则形成了儒家经典注疏的最后高峰。
经学家们以诠释作为思想阐发的主要途径,可以追溯至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论语·述而》载:“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孔子以此奠定了儒家学者“述而不作”的经典诠释传统。而这一传统表现在孔子后学,就是以诠释经典作为其遵述传统的基本表达方式。例如中国儒家大家,汉儒郑玄在写给儿子益恩的《诫子书》中就明确表示,他的人生追求在于“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南宋理学家朱熹在《论语集注》中也称赞孔子“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并称自己的《四书章句集注》“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因而可以说,在孔子“述而不作”的诠释学立场影响下,儒家后学基本以对经典的注疏作为求索“圣人元意”的基本途径。但经典文本是否存在着“圣人元意”,经典注疏又是否能够展现这个“元意”,则是我们当下重新去理解和解释经学家们及其注疏作品时首先必须面对与回答的问题。
经典诠释的独断论特征
实际上,历代经学家在注经活动中所传达的,无一不是对儒家哲学思想体系的新理解与新看法。德国哲学诠释学家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提出,“每一时代都必须按照它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历史流传下来的本文”,因而“理解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
就此而言,文本在每一次被理解与解释的过程中,其“本意”都将被添加上新的维度。尽管在历代经学家看来,“经”这个名称本身就意味着文本内涵的客观化。如东汉班固在《白虎通·五经》中就把“经”和“常道”联系在一起,认为“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直到清人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注“经”时中国儒家大家,也仍旧采取这种立场,认为“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由是观之,“经”所指向的是“天地之常道”。正是中国古代经学家对“经”的这种认识,使得他们的诠释学常常呈现出“独断论”的倾向。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说:“独断论就是纯粹理性没有预先批判它的能力的独断处理方式。”而在中文语境下,“独断论诠释学”作为一种诠释学类型,主要关涉的则是诠释者的“前理解”结构,即诠释主体在诠释文本之前先天设定了对文本的某种理解,并且不从理性的角度对这个理解进行论证。就像郑玄与朱熹等经学家对经典文本所承载的某种“圣人元意”的理解,说明他们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以其圣人元意的信仰为基础,所以诠释者对作为“经”的文本的理解就被先天地限制在圣人所代表的“王道政治”的角度。
但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一旦我们以存在论诠释学为理论视域,去重新理解和解释历代经学家的经典注疏,就会发现尽管历代释经者都预设了经典具有一个统一的圣人元意,但对于这个圣人元意的具体内容,每个诠释者又具有不同的设定。因而从这个层面上讲,历代经学家对经典所承载的圣人元意又具有与其当下历史相联系的效果。这就是说,尽管他们要求在经典诠释的过程中封闭对经典文本的解读,但这个封闭过程同时又是一个不断开放的过程。
考据与义理的诠释学循环
对历代儒家学者经典注疏的研究,最终将会为我们勾勒出一条儒家哲学思想体系发展演变的脉络。对于如何诠释经典以及经典注疏,清代学人曾经作过方法论层面的总结,主要以“考据”与“义理”作为汉代学人与宋代学人的诠释方法。如清代乾嘉汉学的代表人物戴震在《与方希原书》中探讨汉学与宋学之分时说:“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这一对汉学与宋学的评价在今天仍旧占据着重要地位。在清代经学家们的视域中,汉学以东汉经学家郑玄及其郑学为重要代表,郑玄的经典诠释基本上重考据而无义理,而这一观点实际上发源于宋代。自汉代郑学出,历代释经者在诠释经典文本时都必然以郑玄及其郑学为开端,宋学的状况也不例外。在宋人看来,郑玄的成就只在制数方面,因而宋学要站在郑学的基础之上,成就其义理之学。
清人关于考据与义理两分的诠释方法分类模式,实际就脱胎于宋代经学家以他者(以郑学为代表的汉学)为对照进而建立自我身份的历史语境中。但当我们回归原典,考察汉人的经学诠释体系时,就会发现乾嘉汉学对汉学所做的定义并不准确。以东汉经学家郑玄及其郑学为例,在《诫子书》中,郑玄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够“整百家之不齐”,原因在于经典本身所承载的“先圣之元意”,而这一“元意”在他看来就以周公制礼作乐之后所流传下来的《周礼》为代表。因而,郑玄的“经”注虽然的确多重考据,但仍旧蕴含着一套完整的经学义理体系,其考据也以《周礼》所传达的礼制精神为基本指导思想。其根本原因则在于,考据工作必须以一定的“义理”为基础。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提到,我们对文本进行语法分析的过程本身已经被某种意义预期所支配,而这一意义预期在文本分析的过程中会得到进一步的修正,如此便形成了理解的“循环”。所以,从来就不存在纯粹的考据,考据工作必然以对文本整体意义的前理解为指导。诠释学已经表明,正是“前见”为理解与解释提供了积极的可能性。
因而,当今经典诠释研究者们或许不应该再继续以此二分的思维模式来看待古典的经学诠释研究,而要在考据与义理的“诠释循环”基础上,考察历代经典诠释文本所具有的“义理”之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以考古学的视角,考察这一“义理”的“前义理”,即组成其“前理解”的历史堆积物。这样,才能更加贴近历代经典诠释传统的原貌,以此提炼中国传统儒学的思想发展脉络。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