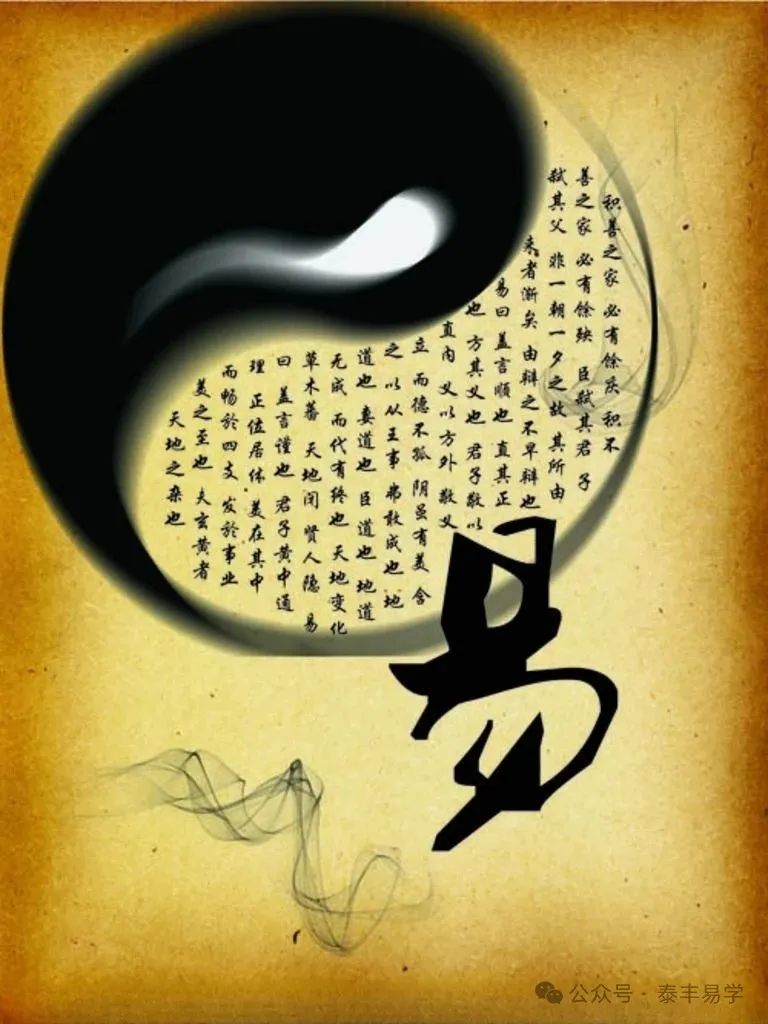从《周易》古经(西周)到大传(战国)的演变
从《周易》古经(西周)到大传(战国)的演变,中间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但一向为人们所忽略的环节,就是《左传》以及《国语》(春秋时代)的筮例体现出来的思想观念:一方面是人的地位的进一步提升,神的地位的进一步衰落;另一方面则是群体精神的进一步加强,个体精神的进一步削弱。从材料上来讲,高亨先生的《〈左传〉〈国语〉的〈周易〉说通解》是非常方便的。高亨先生得出了一条重要的结论:春秋时人基本是从占筮的角度来利用《周易》,但已经开始从哲理角度来理解《周易》了。这个时代,《周易》已经由筮书领域开始跨入哲理著作的领域。
《左》《国》筮例既取象数,也取义理。纯粹象数的如《国语•周语》:(单襄公)曰:‘成公之归也,吾闻晋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终,君三出焉。晋国赵穿杀灵公,迎成公为君,成公此时客于周,归晋时,晋人占筮,得乾之否。按《说卦传》乾为天为君,则《乾》卦上卦为天,下卦为君,这是以君配天之象,应是吉占;但是《乾》卦变为《否》卦,下卦三爻由三阳(乾)变三阴(坤),按《说卦传》坤为臣,则由君变臣。所以其结论为配而不终,君三出焉。纯粹义理的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史墨回答魏献子,引用《乾》、《坤》两卦,证明龙的存在:龙,水物也。……《周易》有之,在乾之妮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剝曰‘龙战于野’。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
但是总体来看,义理的解释正在开始逐渐形成一种时尚,因为它更远离早期龟卜那样的吉凶取决于神定的观念,更符合蓍筮的吉凶取决于人定的观念。而且,单就解释来看,在西周时代,对《周易》古经的解释还是比较严格的,而到了春秋时期的《左》《国》筮例,其解释就更为随意了。例如据《左传•昭公七年》载,卫襄公去世后,大夫孔成子对于立谁为国君拿不定主意。孔成子和史朝都梦到康叔叫他们立元有关周易占卜的英语,但元字有解释方面的岐义:或指名为元的次子,或指名为絷的长子(元有长义,《文言》:元者,善之长也。)。占了一卦,遇《屯》之《比》,结果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解释:史朝根据卦辞元亨,主张立次子元,元亨,又何疑焉!孔成子表示疑惑说:(元)非‘长’之谓乎?于是史朝大发了一番议论,便说服了孔成子。这个筮例说明,决定人事的不是卦辞神意本身,而是人对它的解释,这种解释归根结底其实是取决于人自己的意愿的。
类似的例子,如《国语•晋语》载,后来成为晋文公的晋公子重耳,欲借秦国力量取得对晋国的领导权,占了一卦,得贞《屯》悔《豫》。筮史认为不吉。闭而不通,爻无为也;但司空季子认为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两人各自提出了自己的理由,筮史所根据的是卦象,司空季子所根据的也涉及卦象,但主要是卦名、卦辞。这表明《周易》文本的卦名、卦辞和卦象并不一定一致,这需要人的解释。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左传•僖公十五年》载:秦伯伐晋,卜徒父筮之,吉。涉河有关周易占卜的英语,侯车败。诘之,对曰:‘乃大吉也。三败必获晋君。……三败及韩。这件事的最终结果(三败乃胜)到底是不是出于神意,这很难说,实际上应是取决于当时秦晋两国之间的实际情况的对比;而可以肯定的是,第一次吃败仗无疑是与蓍筮的结论吉相违背的。占筮的吉凶,完全取决于卜徒父的解释。
人们有时甚至连解释也觉得多余,干脆抛开神意,专依人意行事。例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崔武子想娶齐棠公的遗孀,占了一卦,遇《困》之《大过》,史官都认为吉,但陈文子认为不吉:夫从风,风陨妻,不可取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闪。’困于石,往不济也;据于蒺藜,所恃伤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无所归也。筮辞显示的神意是再明白不过的了,但崔武子却无所谓:‘嫠也何害?先夫当之矣!’遂取之。这是因为那时在春秋思潮的背景下,人们已对神意产生了怀疑,认为吉凶取决于人自己。例如《左传•僖公十五年》载,当初晋献公嫁伯姬于秦,筮得《归妹》之《睽》,史苏认为不吉,经过一番解释,其结论是姪从其姑,六年其逋,逃归其国,而弃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虚。后来的史实似乎印证了这一点,但韩简却说:先君之败德,其可数乎!史苏是占,勿从何益!意思是说,当年即使依从了史苏的占断,也是于事无补的,因为吉凶完全取决于人自己的德行。
还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左传•襄公九年》:
穆姜薨于东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
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关于穆姜的未来命运,史官的乐观是依据的对卦名随的解释,而穆姜的悲观是根据的对卦辞元亨利贞无咎的解释。此例的重大意义在于:解释的义理发挥可以否定筮辞本身的吉凶断定。换句话说,吉凶并不取决于《周易》文本所垂示的神谕本身,而取决于求卦者本人所具有的德性,这里就提出了一条重要原则:易不可诬。
根据这种精神,《左传》筮例还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易不可以占险。《左传•昭公十二年》:
南蒯之将叛也(将欲叛鲁降齐)……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坤》卦六五),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者,中之色也;裳者,下之饰也;元者,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恭),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此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能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
这个筮例具有极为典型的意义,表明了这样一种时代观念:《周易》不能用来占断用心险恶之事,吉凶取决于人自己的心地善恶。高亨先生批评:子服惠伯的解释《周易》是琐碎而牵强的,他把内色的黄和内心的忠硬联系起来,把下身的裳和臣下的共又硬联系起来,都是附会之辞,失去《周易》的原意。这个批评当然是有道理的,那就是子服惠伯的解释确实已失去《周易》的原意,然而这正好说明,《左传》筮例已不是《周易》古经的观念了。
吉凶由人,这是西周末期、春秋时期的时代观念:《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史嚣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僖公十六年》叔兴说:吉凶由人。正是在对《周易》古经的这种象数,尤其义理的解释、阐释中,孕育出了《周易》大传的世俗化、哲学化的观念体系。
但是所谓吉凶由人,这个人要看是什么样的人:个体本位的人,还是集体本位的人?在这方面,《左传》筮例也透露出一些消息。其实,上文的举例及其分析已经表明,《周易》解释学化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伦理化。换句话说,人与人的关系原则逐渐地取代了人与神的关系原则。我们看到,这种伦理化就是宗法化,也就是上文所说的非实体化、纯粹关系化。正如上文曾经谈到的,宗是一种无实体性前提的纯粹关系,这样一来,作为第一实体的个体存在着逐渐被消解掉的可能。这是解释学化的一种趋势,就是任何解释都是需要作为前提的某种原则的,这种原则往往不是自我确立的,而是社会的超我(借Freud语)原则。在《左传》筮例中,这种超我原则就是社会群体伦理原则。但是,正如人神关系本身蕴涵着两个维度一样,解释本身也蕴涵着群体的和个体的两个维度,因为虽然支持解释的原则总是群体认同的,但是解释行为本身总是个体进行的,他的个体性体现在他对原则的选择性,这就正如萨特所说,人注定是自由的,因为人的行为总是选择性的。
这种解释的个体精神,在《左传》筮例中依然存在着。上举《左传•昭公七年》的筮例,关于所谓立元究竟立长子絷,还是立次子元,史朝最后提出一个富于个体精神的原则:各以所利,不亦可乎!在春秋时期王权衰落、诸侯力政、各以所利地争霸天下的时势下,诸侯对天子的态度是这种个体精神的一种特定体现。例如据《左传•哀公九年》载,狐偃劝晋文公出兵送襄王归周朝,文公命卜偃占了一卦,得到《大有》之《睽》,卜偃解释: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天子降心以逆(迎)诸侯,不亦可乎!晋侯于是采取了行动。晋文公是一个极富个性的人物,这里他同意天子降心以逆诸侯是理所当然的。诸侯对天子的态度是如此,大夫对诸侯的态度亦如此。例如《左传•昭公三十二年》,鲁昭公被季孙氏逐出而死在乾侯,史墨引《周易》来加以评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其实这并不是新事物,倒是旧传统的再现。王国维曾指出:夏商时代,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于《牧誓》《大诰》,皆称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亦未全定也。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而鲁、卫、晋、齐四国,乂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夏殷以来古国,方之蔑矣。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此周初大一统之规模,实与其大居正之制度相待而成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