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子集的框架相对现在文史哲的分类更接近我们文化本来的面目

我们常说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精深主要体现在经史,博大则体现在子类。
《四库全书》子类分为十四: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
我们研读传统文化,按经史子集的分类看,史类子类集类居多,作为文化核心的经部鲜有深入者。
如今子类跟史类的问题一样,子学与经学没有贯通,用西方的观点和模式来看子类各种学问。
经史子集的框架相对现在文史哲的分类更接近我们文化本来的面目。
用文史哲来归类,文学排在第一,本末倒置,浮华放在了首位。
本立而道生,古人将道德和学问放在第一位,浮华的文学和各种专业技能放到后面。
老一辈看人重人品,绝不会把一个人的聪明当成一件好事,那是一个人的悲哀。
老实最难,我们不缺聪明人,缺的是聪明的老实人,或者叫老实的聪明人。
历史放到第二,看似重视,但西方的史学观跟传统的史学观完全两回事。
哲学放到第三,包括了经学还有子类的部分内容。
哲学是用来想的,中国没有只是思想的人,讲求体认,学而时习之。
中国的学问都是体认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除了这个问题,经学子学放到一起,忽略主流,过于强调支流。
主次不分是文史哲分类的最大问题,丢掉了经史主干是一件悲哀的事。
《四库全书》梳理子类:
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区而列之,名品乃定。其初亦相轧,自董仲舒别而白之,醇驳乃分。其中或佚不传,或传而后莫为继,或古无其目而今增,古各为类而今合,大都篇帙繁富。
可以自为部分者,儒家以外有兵家,有法家,有农家,有医家,有天文算法,有术数,有艺术,有谱录,有杂家,有类书,有小说家,其别教则有释家,有道家,叙而次之,凡十四类。
儒家尚矣。有文事者有武备,故次之以兵家。兵,刑类也。唐虞无皋陶,则寇贼奸宄无所禁,必不能风动时雍,故次以法家。民,国之本也;穀,民之天也;故次以农家。本草经方,技术之事也,而生死系焉。神农黄帝以圣人为天子,尚亲治之,故次以医家。重民事者先授时,授时本测候,测候本积数,故次以天文算法。以上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也。百家方技,或有益,或无益,而其说久行,理难竟废,故次以术数。游艺亦学问之馀事,一技入神,器或寓道,故次以艺术。以上二家,皆小道之可观者也。诗取多识,易称制器诸子百家 道德,博闻有取,利用攸资,故次以谱录。群言岐出,不名一类,总为薈稡,皆可采摭菁英,故次以杂家。隶事分类,亦杂言也,旧附於子部,今从其例,故次以类书。稗官所述,其事末矣,用广见闻,愈於博弈,故次以小说家。以上四家,皆旁资参考者也。二氏,外学也,故次以释家、道家终焉。
夫学者研理於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徵事於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馀皆杂学也。然儒家本六艺之支流,虽其间依草附木,不能免门户之私。而数大儒明道立言,炳然具在,要可与经史旁参。其馀虽真伪相杂,醇疵互见,然凡能自名一家者,必有一节之足以自立,即其不合於圣人者,存之亦可为鉴戒。虽有丝麻,无弃菅蒯;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在博收而慎取之尔。
叙要将子书界定为“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
这种分法遵从古人说的本末,经史为本,子集为末,以经史衡量诸子之是非,所有著作皆“考信于六艺”。
先秦之书,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围绕天地规则来论述各自的学说,说法不尽不同,核心价值相同。
春秋战国时期,道论已经支离破碎,庄子说“道术将为天下裂”,各家各有各的说法,没有统一的认识。
“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区而列之,名品乃定”,说的是西汉经学刘歆为新校本图书编的总目录,从此,各种图书有条不紊地展示在读者面前。
七略分为七部三十八类,条分缕析当时的各种文化流派,以辑略的形式评述了各种文化学术的兴衰分合,以各书叙录的方式详细介绍各种著作的真伪是非。
可惜的是,《七略》早已亡佚,《汉书·艺文志》删了《七略》中的辑略,将天下图书分为六类: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和方技略。
六类三十八种,保留了刘歆对当时书籍的分类,胡应麟先生在《少室山房笔丛》说:“首之辑略,以总集诸书之要,则分列品题,实六略耳。班固《艺文志》,增入三家,而省其十家,共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篇,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歆原书三万三千九十卷,固节其猥冗,仅得十之三四”,“然《七略》原书二十卷,班氏《艺文》仅一卷者,但存其目耳”。
“其初亦相轧,自董仲舒别而白之,醇驳乃分” 说的是董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
经学和诸子的区别在哪里:醇和驳,在董子看来,经学醇正,诸子驳杂。
读过四书五经和诸子百家,再有人生各种教训和经验,两者区别非常明显。
个人的经历和看法,经学醇厚,最安全最稳妥最适合每个普通人的作品,如五谷一样,每个人都需要。
开始的时候,诸子也没有分得那么清楚,这种区别,较早的资料,一是《庄子·天下篇》,
二是《史记》最后一篇引用了其父司马谈的一篇文章《论六家要旨》。
文章将诸子百家归结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
他认为,六家都是为了治理天下,只不过角度和方式的不同而有区别,认为儒家富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社会责任感。
叙要之意,分类从《汉书》开始明晰,主次从董子开始清楚,“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區而列之,名品乃定。其初亦相軋,自董仲舒别而白之,醇駁乃分。”

二三段,《四库全书》将子部十四类分为四组:
治世者所有事: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
小道之可观者:术数、艺术。
旁资参考者: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
外学:释家、道家。
从分组的情况看,跟历代一样,以儒家为正宗,叙要认为“儒家本六艺之支流” ,为“孔孟之正传”。
在古人眼里,儒家是最高级的实学,读书以明理,明理以致用,是一门重视社会实践的大学问和大事业。
道德和法律是人类文明前进的两道堤坝,传统的中国更注重道德,道德是教化的结果,恰恰是社会文明的体现。
儒家正统等贵贱均贫富的大同思想总在社会失序的时候拨乱反正诸子百家 道德,当资源分配平等公正的时候,社会迅速发展。
其次,重视实学,除了儒家,将农家、医家、天文算法三类升至前六位。
实学相当于科学技术,一直广泛流传的说法,中国一直是实用主义,缺乏理论与体系,只有技术没有科学。
科学技术建立在西方的理论和逻辑上,实学则建立在传统格物致知的学问基础之上,就好像中医建立在中医的理法基础上,西医建立在西方的医学认知上一样。
汉代的时候,实学已经非常发达。
天文上,制订出中国完整的太初历指导当时的农业生产,根据不同的节气来种植农作物。
水利上,相继建成了龙首渠、白渠、六铺渠等大型水利工程,形成了引渭渠系、引泾渠系、引洛渠系三大渠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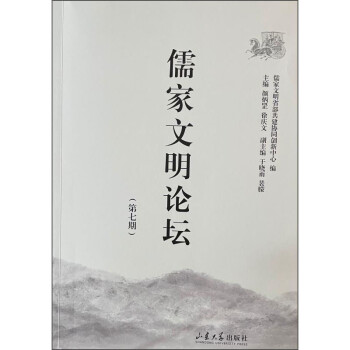
铁在中国,春秋战国已有,《孟子》已有铁耕的记载,战国的兵器已有用铁铸造。
冶铁技术到了汉代兴盛起来,各种农具广泛使用铁器,其次是兵器和日常生活用具。东汉发明水排,同时发明低温炼钢法,从此铁制的武器取代铜兵器。
汉代造船制车也也非常先进,汉武帝时候所造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
中国向以陶瓷和丝绸闻名于世,汉代的丝织业和陶瓷工业非常发达,质量相当好。
西汉时,已经懂得基本的造纸方法,到东汉,蔡伦改进造纸工艺,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纸。
实学发展并不是简单的经验累积,背后有一个完整的体系。
如东汉的《九章算术》是算术专著,提出了分数的运算问题,记录了盈不足问题,方程提出了负数及其加减的运算法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一部应用数学著作。
其三,术数艺术归为小道一类,用于修心养性,进德修业。
在古人看来,易道洁静精微,研究天地规则的典要,术数是易学的支流,小术小道,纠缠夹杂。
《术数类》小叙说:“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要其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皆《易》之支派,傅以杂说耳。”
信者信其有,不信者信其无,不管有无,术数是一门技术,涉及处理问题的智慧,何事该管何事不该管,何人能帮何人不能帮,什么时候什么能力做,什么身份什么地方做,有什么规矩按什么规矩做……
这些都是问题,看了做了,如蝴蝶效应一般,有所牵绊搅动,没有经史的沉淀和修养,惹事生非居多。
相对修齐治平天下的经史之学来说,艺术也只是边缘化的存在。
四库艺术类明确了四个子目:书画、琴谱、篆刻、杂技。
杂技相对驳杂,“名品纷繁,事皆琐屑”,杂技子目下棋类为主的游戏类书和乐府为代表的歌舞类书籍。
古人眼里的艺术,重技术,更重意境和神韵,“一技入神,器或寓道”。
如今的艺术,作品已经不再是如其人如其学如其志的呈现,而是形式至上和技术至上。
当形式与技术成为唯一的时候,艺术远离了文化的担当,远离了以人为本的艺术传统。
艺术和人生,艺术的广大和人生同其广大,艺术的深邃和人生同其深邃,离开了人生的艺术,无异于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在古人看来,艺术的基础是个人的学养和修养,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是根本,境界要求中和、典雅、含蓄,只是用形式和技术来代替传统艺术,削大象的足,适老鼠的履。
其四,广采博取,各种异闻、杂说、笔记的书籍作为参考也收录进子部,分为四类:谱录、杂家、类书和小说家。
谱录专门收录各种图谱的书目,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三类,大家熟悉的《茶经》收在食谱类,食谱类收录了与茶、酒、糖、蔬食及各种食物原料、作法和历史的书籍。
“以立说者谓之杂学”,杂家是四库中收录内容最多的一类,包罗万象,把当时不能具体划分的诸子著作统统列入,分为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
类书专门供人查阅的、辑录各个门类或某一门类的工具书,四库收录六十四部书籍,共六千九百七十三卷。
类书不但是搜索引擎一样的工具,还是书籍另一种形式的保存,类书类小叙说:“古籍散亡,十不存一,遗文旧事,往往托以保存,《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诸编,残玑断璧,至捃拾不穷。”
小说家类书籍记载故事轶事小说的汇编,小说家类分杂事、异闻、琐语三属。
其五,将带有宗教色彩的释家和道家归到外学。
传统社会是文教社会,也可以叫尚文政治,以文教为中心,宗教不占主导地位。
文教社会可以叫做读书人的政治,传统上的读书人并不是现在所说的知识分子,叫做士。
钱穆先生的看法,中国是一种士人政治,士谋道而不谋食,上则从事政治,下则从事教化,只为大群着想, 不为一己着想。
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宗教,教给他们德行和责任,教育他们服务社会,这是西方文明的特点。
有不少人讨论中国有没有宗教的问题,关键是宗教的本质是什么?
深入了解的话会发现,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从犹太教中分裂出来的,他们又各自分裂成不同的教派,还有许多不属于以上三种的教派。
伊斯兰教中分为什叶派、逊尼派和苏菲派,教里教外又有无数派别。
印度主要的宗教是印度教,分裂情况更极端,可能连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印度教到底有多少派别,宗教冲突在印度一直是一个近乎无解的难题。
可以说,分裂是宗教本质之一,奇怪的是,同一个信仰的人又会团结一致对外,越团结越分裂,越分裂越斗争,斗争越来越激烈,宗教冲突成为社会动荡的主因之一。
文教着眼在和合,在群体里面做个体,个体有责任带好群体,个体有责任维持自己的尊严,但是也维持自己和群体的关系。
弊端在贼与弊,不是每个人都公事公办,文山会海,总有有人利用文书不断抠字眼,一条条文书进出实现私利。
尚文政治最容易产生伪君子,汉唐质朴,问题少一点,宋代之后,文大于质,文过饰非的例子不胜枚举。
不是每个人都有非常好的学养和修养,尚文政治最容易在基层出问题,导致吏治败坏。
制度不清,职责不清,责任落实不到位一直是历代的大问题。
公允来说,没有完全好完全坏的文化传统,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化传统,即使再好的传统也会因时间的推移而衰落。
一个文明有一个文明的传统,问题在知人论世,根据当时实际情况而看问题,清楚认识我们的传统,不是一味地否定和批判。
最后一段强调经史为本,淳淳告诫,“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读经明是非曲直为根本。
“徵事於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读史明得失进退为基础。
四库叙要子部说得明明白白,经史是根本,其他都是枝叶,作为根本的延伸和补充。
后世儒家的著作,叙要也说的非常中肯,是“六艺之支流”,著作大都有门户之见,这也是事实。
不过,历史总会出现几个大儒,“明道立言,炳然具在”,跟经史互参。
收录其他著作,叙要说:然凡能自名一家者,必有一节之足以自立,即其不合於圣人者,存之亦可为鉴戒。
自成一家的都有可取之处,即使跟经史观点不一样,也可以作为借鉴。
最后一句,“虽有丝麻,无弃菅蒯;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在博收而慎取之尔”。
可见,我们的文化没有那么狭隘,兼容并包是本色,学问博大,贵在博收而慎取。
站在文化本位的角度看,如果根本能立起来,消化吸收西方文化,可以在子类再列一个西学类,我们的文化传统,有足够的智慧与气度吸收外来文化。







